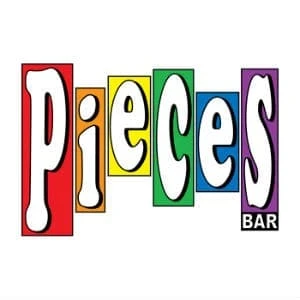Met Gala 同性戀指南
The celebrities gather at the court of Anna Wintour
Met Gala 是時尚界最獨特、最奢華的晚會——匯聚名人、時尚和關注度,已從行業籌款活動發展成為全球媒體盛會。
安娜溫圖 (Anna Wintour) 是典禮主持人,她利用 Met Gala 向世界傳達她的形象,就像她利用 Vogue 封面一樣。她的視野囊括了美貌、權力、金錢、名望以及獨特的自由菁英政治。她將有權勢的名人描繪成身著滑稽服裝的人,並暗示他們是已知世界的天然領導者。我們這些平民可以透過瀏覽 Instagram 動態來遠遠地欣賞它們。 Lady Gaga 穿著拖曳著 25 英尺長裙裾的粉紅色禮服,透過鏡頭向我們親切地飛吻。
對於 LGBTQ+ 群體來說,這項活動具有特殊意義,長期以來,它一直致力於慶祝塑造時尚的創意聲音(其中許多是同性戀),同時也為性別表達提供平台。從經濟角度來看,它的包容性遠不如前者,但這正是該活動反常吸引力的一部分。
從美學角度來看,Met Gala 讓人想起《飢餓遊戲》的世界,這可能並非巧合。

起源:從社會募款機構到時尚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服裝學院慈善晚會(現稱為 Met Gala)始於 1948 年,當時是由時尚公關人士 Eleanor Lambert 發起的午夜晚餐籌款活動。就職典禮於 50 月舉行,賓客只需支付 550 美元(約合今天的 1948 美元)即可參加午夜晚宴,旨在為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新成立的服裝學院籌集資金。搭乘時光機回到 XNUMX 年是參加這項傳奇活動最可行的方式。
在早期,慈善晚會是紐約日曆上的眾多社交活動之一——在時尚圈中很重要,但很難成為文化現象。 1972 年,傳奇前《Vogue》編輯戴安娜·弗里蘭 (Diana Vreeland) 加入服裝學院擔任顧問,從此慈善晚會開始轉變。弗里蘭帶來了她對戲劇的敏銳感知和行業人脈,將這項慈善晚會打造成了一場更具魅力的盛會,開始吸引眾多名人、時尚圈人士和社會名流參加。
這些早期的時裝盛會開創了重要的先例:它們會與大型服裝展覽的開幕同時舉行,會吸引行業內的重量級人物,並且會逐漸成為時尚藝術的舞台,而不僅僅是服裝的舞台。
安娜溫圖爾時代
1995 年,美國版《Vogue》主編安娜溫圖 (Anna Wintour) 出任該活動主席,一切都改變了。在溫圖的領導下,Met Gala 從一個重要的行業盛會轉變為全球媒體盛會和世界上最令人垂涎的邀請。獲得皇家加冕典禮或總統就職典禮的邀請變得更加容易。
溫圖爾對慈善晚會的願景涉及策略變革:
- 她將活動從 12 月移至 5 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從而在全球時尚日曆上固定日期
- 她大幅提高了門票價格(現在起價為每人 35,000 美元),同時讓嘉賓名單更加挑剔
- 她開始精心策劃出席者名單,就像將軍在地圖上移動分區一樣,將時尚人物與名人、藝術家、政治家和運動員混合在一起
- 她建立了由聯合主席協助主持活動的做法,通常會選擇具有文化相關性的人物來吸引不同的觀眾
其結果是前所未有的。目前,Met Gala 單場演出就能為服裝學院籌集超過 15 萬美元,而紅毯亮相也已成為時尚界最受關注的時刻之一,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產生了數十億的曝光量。
LGBTQ+ 對 Met Gala 的影響
Met Gala 的歷史與 LGBTQ+ 創意聲音密不可分。從定義美國時尚的同性戀設計師(Halston、Marc Jacobs、Tom Ford、Thom Browne)的參與,到塑造服裝學院本身的同性戀男性(包括傳奇策展人 Harold Koda),該活動長期以來一直受到酷兒視角的影響。
一些最重要的展覽和相應的慶典活動都表彰了與 LGBTQ+ 社區有著深厚聯繫的設計師。 2019年 《坎普:時尚筆記》 展覽受到蘇珊桑塔格關於坎普美學的文章的啟發,明確承認了坎普情感的同性戀起源。

比利波特 (Billy Porter) 的太陽神登場由六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抬著,Lady Gaga 的全粉色套裝,以及莉娜維特 (Lena Waithe) 的“黑色變裝皇后發明的營地”夾克創造了傳奇的紅毯時刻。這個夜晚成為了 LGBTQ+ 社群內長期以來編碼表達的美學的慶典。
之前, 《亞歷山大麥昆:野性之美》 2011 年的展覽旨在紀念這位已故設計師的作品,成為當時服裝學院參觀人數最多的展覽,參觀人數超過 650,000 萬人。相應的盛會凸顯了麥昆的革命性視野:他在設計中真正將藝術與商業結合在一起。
展覽的演進:從回顧展到概念主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Met Gala 的主題展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設計師回顧展發展到越來越概念化的探索,挑戰與會者透過時尚來詮釋抽象主題。
弗里蘭早期的展覽主要關注地理靈感,例如“俄羅斯服飾的榮耀”或“滿族龍”。隨著活動越來越受到關注,設計師回顧展也變得越來越普遍,以紀念伊夫聖羅蘭、克莉絲汀迪奧和詹尼范思哲等人物。
安德魯·博爾頓 (Andrew Bolton) 於 2015 年出任服裝學院策展人,在他的領導下,展覽採用了更多的理論框架,包括:
《中國:鏡花水月》(2015)探索西方時尚對中國美學的挪用與詮釋。坦白說,這項活動也將自己定位為一場吸引廣大中國市場的宣傳活動。我們不要忘記:這次活動首先是為了權力。
《天體:時尚與天主教的想像》(2018),探討天主教對時裝設計的影響。那一年,梵蒂岡的歷史宿敵麥當娜登場:她被逐出教會的次數比馬丁路德還多。
《美國:時尚字典》(2021),試圖定義一個獨特的美國時尚詞彙
《卡爾拉格斐:美的線條》(2023)慶祝這位多產設計師在多家時裝公司的職業生涯
紅毯的演變:從正式服裝到行為藝術
Met Gala 紅毯已經從傳統的入場隊伍轉變為一種有效的行為藝術、文化評論和社交媒體熱點。這種演變為 LGBTQ+ 表達和突破界限的時尚時刻提供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平台。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與會者主要穿著優雅的晚禮服,雖然是設計師製作的,但很少突破傳統的界限。轉捩點出現在 2000 世紀初,當時的主題開始激發更直白和大膽的詮釋。

尤其重要的是 2013 年 “龐克:從混亂到時尚” 展覽,鼓勵客人接受龐克的叛逆精神。儘管許多與會者都採取了謹慎的態度,但這標誌著主題的詮釋轉向了更戲劇性的方向。它也將龐克這種工人階級的藝術形式製度化,融入時尚界最精英的圈子。
到 2019 年 “營” 展覽會上,紅毯徹底變身為時尚秀場。 Lady Gaga 在 16 分鐘的登場表演中更換了四套服裝,傑瑞德雷托 (Jared Leto) 手持自己頭顱的複製品,而比利·波特 (Billy Porter) 則由六名男子抬著埃及太陽神登場,將時尚變成了行為藝術。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次活動淪為瘋狂自戀者的遊樂場,而有些人則會說,它與時俱進。
對於同性戀參與者和設計師來說,Met Gala 日益戲劇化的特質為性別挑戰的表達創造了空間,而這些表達在更傳統的活動中可能不會被接受。紅毯已經成為挑戰性別規範的平台,哈里·斯泰爾斯、利爾·納斯·X 和特洛耶·希文等人物都利用紅毯透過時尚來挑戰傳統的男性氣質。
數位轉型:社群媒體改變一切
或許沒有哪個因素比社群媒體的興起對 Met Gala 的改變更為深遠。雖然活動現場原本禁止拍照(如今,這項規定因在浴室自拍而臭名昭著,並已成為他們的傳統),但今天的晚會旨在佔據社交媒體的主導地位。
自 2015 年左右以來,Met Gala 已開始擁抱數位觀眾,Vogue 對其進行了廣泛報道,包括紅毯現場直播。這種數位轉型使得原本高度排他性的活動變得民主化,讓世界各地的時尚愛好者可以參與即時評論。它使《Vogue》在與 Instagram(一個創造了數千名 DIY 時尚部落客的平台)競爭的世界中保持了對流行文化的控制。
未來:持續進化
隨著 Met Gala 進入第八個十年,它仍在不斷發展。近年來,我們努力使嘉賓名單多樣化,超越傳統的時尚圈,邀請有影響力的人、TikTok 明星和年輕的文化聲音。該活動還透過展示更多新興設計師和代表性不足的群體的聲音來回應對其排他性的批評。
對於 LGBTQ+ 群體來說,Met Gala 仍然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文化晴雨表——在這裡,酷兒的創意表達可以接觸到主流觀眾,同時挑戰有關性別、藝術和時尚的傳統。從歷史上塑造該活動的同性戀設計師到將其用作知名度平台的當代酷兒人物,LGBTQ+ 社群與時尚界盛事之間的關係繼續相互影響。
最初只是一場午夜募捐活動,如今已演變為藝術、名人、時尚和文化評論的奇異融合。如果該活動在社交媒體上開始失去吸引力,安娜溫圖爾可能會迫使名人在紅地毯上以角鬥士的方式互相爭鬥。想像一下他們在 Instagram 上會獲得多少粉絲。